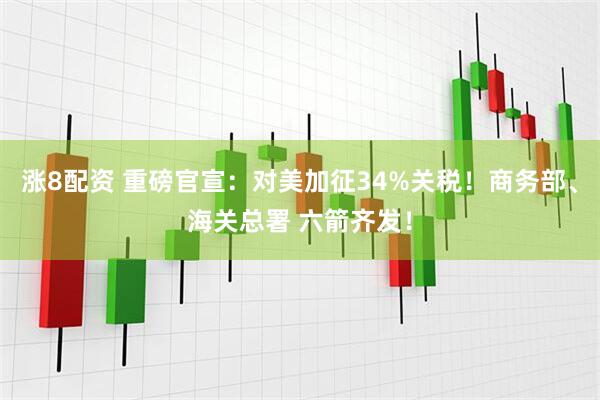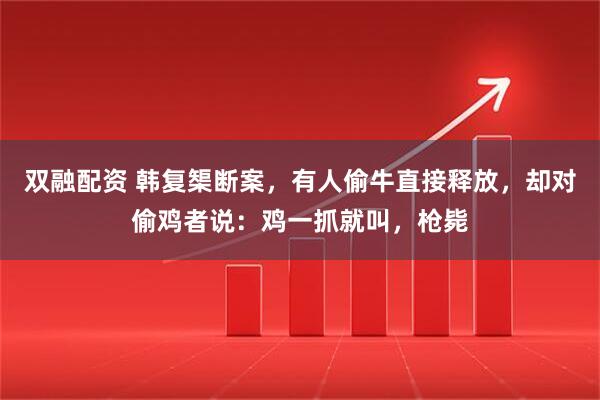
1930年9月16日清晨,济南府衙的铜钟刚敲过三下,一支由军乐队、号兵和荷枪宪兵组成的队伍沿大明湖畔而过,这支场面不小的行列正护送新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前往省府大堂。街坊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排场,更熟悉的是随之而来的“韩家公堂”。只要屏风立起、绳索摆开、军棍靠墙,那一天济南就像进了临时戒严——人们不敢随意上街,却又管不住好奇,远远张望,看这位“韩青天”又要如何拍板生死。
韩复榘生于1890年,在直系、奉系军阀混战间摸爬滚打,对枪炮的信任远胜对法条的敬畏。孩子气的嗜好也带到官场:少年时代翻烂了《包公案》《施公案》,于是动不动就要给自己补上一顶乌纱。审案时他不爱听卷宗,只爱看人。犯人一站出来,他先抬手揉额头,似在推敲,其实多半已定成败。手往右摆,活路;手往左挥,枪口。省里负责司法的官吏背地里暗骂:两片嘴皮碰一碰,这便成了山东省的全部法典。
有意思的是,韩复榘偏偏喜欢挑极端的案子下手。济宁府送来一桩案子:甲偷牛,乙偷鸡。牛市价六七十块大洋,鸡值不过几吊钱。旁听百姓觉得天平早倾向乙。可韩复榘冷不丁来一句——“牛不吭声,偷得倒也干净”,右手轻轻一摆,甲当场获释。轮到偷鸡的乙,他忽地侧头笑了:“鸡一抓就叫”,左手猛挥,火速枪决。那句七个字的评语被街口茶馆转成顺口溜,半日传遍济南府。老东家们谈到此事都悄声叹气:这位韩主席颠倒黑白,却又无可奈何。
戏剧性场景不仅发生在公堂。1933年初夏,韩复榘微服逛章丘集。卖鸡的大娘与布店掌柜争抢一只老母鸡,围观的商贩七嘴八舌,局面一度胶着。韩复榘掏出两块银元,豪气拍在案板:“鸡归我。”当众割喉,鸡嗉子里尽是红高粱颗粒,正应了老大娘所言。掌柜和帮腔的豆腐匠瞬间傻眼,被扒裤泼麻酱,豆腐匠还被勒令“清理”掌柜后背。围观群众看得瞠目结舌,这位省主席用一出闹剧把曲直分得明明白白,也把自己粗鄙又机警的性子暴露无遗。
同年秋天,他又因一支派克金笔大动干戈。那是美国货,省府文书郭浚瑜被偷后哭诉无门,韩复榘立刻点名三昼夜破案。分局长徐吟滠束手无策,只好领骂。第四天清早,韩复榘化身“老王掌柜”,踏遍济南旧货摊,连一碗羊汤都顾不上喝。终于在茶馆盯上一名满身插笔的王相坊。遗憾的是,派克笔没追回,人却被吓跑。韩复榘面子挂不住,自掏腰包从上海买来同款,才算给文书一个交代。四个月后,他偶遇王相坊当街补鞋,反倒将其带回省府安插闲职。有人猜测,王相坊的“相坊”与韩复榘字“向方”谐音,韩对兆头迷信,不敢下杀手。
在韩复榘的裁决里,法律常常让位于性情。错杀“小道”的故事便是例证。那年深秋,民主人士沙千里派勤务员送信,小伙子好奇凑近公堂,不慎被当成囚犯。韩复榘只听到“送信的小盗”,未及分辨,手已向左。落日时分,枪声回荡在大院墙外。事后沙千里找上门时,韩复榘才后知后觉,赔出一千块现大洋了结。十五岁的少年命丧走廊,衙门口的老槐树下多了一块无字碑。
有人骂他草菅人命,也有人夸他“有魄力”,两种评价搅在一起,像胶东的咸糟鱼,又腥又劲道。不可否认,他在山东推行过减税、修路、兴水利,一度让士绅与农民都得到实惠。但只要回到断案现场,所有善政都被那句“我的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,就是法律”盖了戾气厚尘。试想一下,一省公堂若仅凭个人喜恶,公平二字自然无处安身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韩复榘奉命率部守津浦线,却因擅自撤退触怒中央。当年12月24日,他被扣押于开封。短短四个月后即枪决,从此天下再无“韩青天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最后一次走进军法处,已不是审案人,而是被审者。行刑前,他低声抱怨:“此处无包公。”究竟是讽刺自己还是埋怨命运,旁观军官说不清,也不敢问。

韩复榘的故事在山东乡野讲了几十年,一半荒唐,一半血性。人们爱听那些离奇判决,更多时候也只是笑谈。毕竟,自诩青天却无法摆脱军阀逻辑,终究难逃法纪真正的判决。
联丰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精选期货配资 香港潘秋丰
- 下一篇:没有了